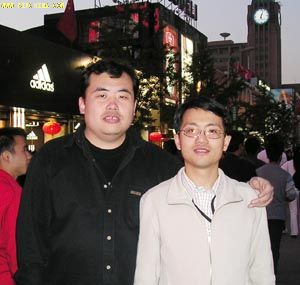
顾炜和北京棋手刘彤
1996年10月的一个周六,我在人民公园一个很偶然的情况下遇到了李北峰先生。那时的北峰独自一人在摆弄棋子,丝毫没有受到周边的干扰,一副怡然自得的样子。说起来,当时比较可笑的是我曾忐忑不安地猜想北峰是否是下彩棋的。只是因为对棋有种莫名其妙的亲切,我终于还是走上去询问是否可以下,北峰欣然同意。两个人究竟下了多少局,早就记不清了,唯一还记得当时自己不断暗地叮嘱自己:不能输太多。此外,有一局棋令我印象深刻,当我四三自以为胜时,北峰借着防御已经活四了。这对我的触动比较大,毕竟当时我在学校里面下五子棋也是数一数二的。那时我对北峰计算之精深,由衷感到佩服。尽管他一再谦虚地表示纯粹碰巧。临别之际,北峰邀我下周继续来交流,并表示将向我推荐一位高手。一个礼拜飞快就过去了,当再次来到人民公园,北峰已经和一位敦实的汉子在下棋。通过介绍,我认识了李洪斌,当时“上文杯”大赛的季军。
那时候,和洪斌下棋是件比较痛苦的事情。因为我当时还是野路子,虽然有了一定的计算能力,但是不懂布局、不懂定式,不知道先手必胜,一旦对局,先手必攻,后手苦防。因此在和洪斌的对阵中吃尽了下风,简直怀疑自己是不是在下五子棋。到现在为止回想起来,和洪斌那三个礼拜的对局是最集中的。虽然在33局中只胜了3局,但是我明显感到实力的提
高。一是初步形成了禁手概念,二是掌握了一定的实战攻防技巧,三是初步掌握了2种必胜定式。第一次的11局,输的浑浑噩噩,最后那局多半是洪斌相让,估计是怕坏了我的自信心。第二次的11局,虽然还是输,但是我已经能看清怎么输的了,最后1局的胜利固然有对手的疏忽,但是个人还是把握了机会。第三次的11局,主要输在经验,有些对局一度还是优势或平衡的,但没有把握住,最后一局双方都很认真,依稀记得是“流星局”。当时洪斌一度攻的很厉害,我几乎都认为要输了,但每次还是顽强地找到了唯一防,尤其是最后使得局面逆转的唯一防,那是洪斌和北峰都疏忽了的手段。由此我踏上了一条全新的五子棋之路。
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实战是在人民公园和曾打进“上文杯”20强的俞成军先生间的五番战。那也是俞先生第一次来活动,北峰推荐我和他下。结果一开始连输两场,还被抓了禁手。北峰在旁边看着,说了句:你可是学了好长时间的了。那时的我只有18岁,年少气盛,脸当时就红了。在接下来的三局中,我下的格外认真,连下三城,以3:2取胜。现在回想,实在是因为年轻的缘故呀。
在人民公园下了一段时间,陆陆续续见到了不少棋友。章志强、柳旭伟、罗锦伟、高云海、赵锴、张奕翔等。各人的棋自有特色,相当程度上也体现了这个人的性格。同现在相比,从某方面来讲,那时的棋更有意思。
1996年,虽然我提高了不少,但是相对于处在第一梯队的李洪斌、章志强、柳旭伟、赵锴、张奕翔、李北峰来说,还差着一个层面。我的全体提升是在1997年初,还要归功于北峰。有一天,天气极为寒冷,我和他在人民公园很久没有等到其他人来,于是一起到新世界商厦顶楼的美食广场。在那里,我们边吃边下,一共进行了7局,我以4:3取胜。就是这次以后,我感到我的棋硬起来了,不再是那么软绵绵的了。而且下棋有了自己的想法和思路,不再是只依靠单纯的计算了。此后,我同第一梯队之间相差只在毫厘之间,捅破这层窗户纸只是时间问题了。所以,直到今天,我还是很感激北峰那甘为人梯的精神。在五子棋上,北峰既是我的朋友也是我的老师。
1997年夏天,《新民晚报》在体育版不很显眼的地方登载了一条消息,大意是北京五子棋代表队来沪交流,上海棋院安排了时间和地点,欢迎广大爱好者届时报名参加。当得知这个消息后,我们各自开始准备。北峰也同上海棋院取得了联系,确保我们这些人能得到交流机会。
记得交流前的一个晚上,章志强因为路远,到我家住宿。晚上我们两人很晚才睡,还对明天的情况进行了推测。第2天一早,我们赶到上海棋院。虽然只有8点不到,已经有不少人在排队了。我们是以北峰五子棋俱乐部的名义集体报名的。来的这些人有认识的,有闻名的,也有不认识的,但是个个都是一个方面的“棋王”。其中,一个年纪较大的长者高谈阔论吸引了我们,而且他还带了一些日本原版的五子棋书籍。这个引起了我们的浓厚兴趣,经过攀谈,我们知道他叫顾伟国。
时间超过9点后,由曹志林陪同的北京五子棋代表队出现了。一个大胖子带头,后面来了一长串,男男女女,统一服饰,胸佩的是京都连珠社还是RIF的徽标却记不清了。大家对其他人不熟悉,但是对这个大胖子可认得,除了通过中央电视台五套就是通过一些五子棋书籍了。没错,这就是那威。当时由于人多,最后采取每人五元发一号的报名办法。幸亏北峰已经联系,我们全部取得了号码。
那时北京镇守第一台的是李栋,依次是白涛、陆遥、邵小冬等,采取多面打、上海方面布局的形式。洪斌、赵锴、章志强、我,还有获“上文杯”第5名的王伟明被安排在第一台。我布局金星,李栋没有交换,我们按照大定下,到20几手,白棋变了一招,结果我考虑了一会儿,干净利落的VCT取胜。这天上午,李栋挺背的,因为他不知道他所面对的都是上海第一层面的选手。结果只和了一局,其他都输了。我们当时很高兴,认为北京选手也不过如此。
结果下午,对方提出上海和北京来个四对四的对抗。为了安全起见,北峰将我摆在第一桌,依次是李洪斌、赵锴和王伟明。双方还打钟,这也是我第一次正式参加比赛并打钟。等到实战,我和李栋下斜月,我拿白棋。我留下了现在认为的一打,当时的研究和现在没法比,第6手试图导回金星变化。结果黑7没有下日本定式书上的走法,当时认为李栋考我。但是仔细算算,白棋还真没什么好办法,白8、10可能随手了点,因为当时把日本的五手二打定式书当成绝密件,上海得到这些资料很不容易,是靠前面提到的俞先生从北京购来的复印件(事后听说似乎是资料换资料,为此上海还起了点小小的风波),我们自己再复印的。当时的条件有限,复印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所以整个上海也就那么几本,我们把这个基本当作金科玉律的,怎么会出现书上没看见过的,一定是不好的或败招。当时实战的想法基本就是这样的。现在看来,太教条了,有点可笑。
黑11以后,我发现形势不妙,然后低下头盯着棋盘计算,越算脸越红,因为我看到自己在30几手以后怎么输的。整整20多分钟,我没找到强防,但是抱着侥幸心理,我继续下。最后,李栋的胜法和我自己算到的一模一样,我有点震撼。我是第一个结束战斗的,在复盘中,李栋告诉我黑7是日本奈良秀树八段(当时)发明的,优势非常明显。由此,我真切感到双方确实存在很多差距。说侥幸,早上我的取胜才是真的侥幸。因为那是前一天晚上我复习的最清楚的一个变化。随后,李洪斌和赵锴也相继告败,只有王伟明取胜,为上海稍稍挽回了面子。
对抗赛期间,那威为广大上海棋友进行了现代五子棋的讲课。罗锦伟由于没有参赛,成为现场最活跃的听众。比赛结束以后,大家闲聊。老那和我们聊了很多,不仅讲了很多比较先进的技术理念,还介绍了如何推广普及五子棋的一些办法和举措,对我们收获真的很大。也就是那时起,为了帮助上海五子棋发展,我们接受了老那的建议,一致推选罗锦伟担任两地之间的联络员,以后就成为了RIF中国事务部上海联络处的联络员。
那以后,上海五子棋发展有了很多新起色。虹口公园有个五子棋活动地点(1997年春节后,我们不再去人民公园活动)的消息被很多人知道,一时间虹口公园非常热闹。陆震、张浩、丁正荣、李滔、宋云涛、黄民城、葛凌峰、郭朝辉、张捷等相继前来活动。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老顾同志,成为了一名狂热的五子棋棋手,不但定期来下,而且非常敬业。一次突然下雨,他和洪斌有局棋没结束,结果我们都躲雨去了,这两位撑着雨伞继续,一时被传为佳话。那个时期可能也是老顾下棋最集中,棋力最能得到发挥的黄金时期。现在想想,老顾那时候的性格已经注定他将成为上海五子棋发展困难时期的关键人物。如果1998、1999年没有老顾的话,真不知道今天的上海五子棋会走向何方?
此外值得一说的是,那时我们不管平时还是比赛,大家都是随身带着空白棋谱,尤其是北峰总是带着一叠放在包里,只要下棋我们就记。有时谱用完了,记在脑子里,回家赶快补上,然后再复盘。通过记谱复盘,我们总能有更多的新收获。那段时间也真的是最难忘、最长棋的时候。
前尘往事如烟云。现在回忆十年前的一幕幕,就象昨天发生的。喜悦、激动、悲伤……各种情绪一起涌来,心情极为复杂。如果要简单的说,那就是:十年风雨路,十年连珠情。此情最珍贵,一代连珠人。(作者:顾炜)
转载请注明出处。

 相关文章
相关文章 精彩导读
精彩导读 热门资讯
热门资讯 关注我们
关注我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