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匆匆穿上家人衣服,胡亥却是生具异相,两只胳膊比普通人长出一寸左右,那衣服穿在身上,高矮胖瘦虽然合适,却把两只手腕子给光秃秃地露在了外面。虽说也并不特别显眼,众侍卫却是看惯他宽衣博袖的穆穆天子容,如今乍一见这个缩手缩脚的小厮打扮,忍不住都有些失笑。
“就这样了!”胡亥一跺脚,道:“这就去吧,我倒要看看这个天下第一生得什么模样!果然是三头六臂,我便封他为国师!”
“陛下若真封他国师,他也就不会再是天下第一了。”
这句话胡亥却不懂,扭头看向蜀王,只听他婉婉解释道:“臣弟的意思是,此人以天下第一的本领为陛下所知所用,可若真为陛下所用了,他便立刻不再是棋坛中人人思慕的天下第一了,”微微一笑后又补充了一句:“这正是庙堂的可怕之处。”
这句话的意思却深奥了,胡亥还没完全明白过来,已到正厅。
这时远远便看见阶下走来一对年轻男女。男的一袭白衣,通身上下浑无装饰,神色间澹澹然地不起波澜,宛然常人。倒是跟在后面的那个女子叶裙如荷,珠缀如露,怀里斜抱着一只长长的木匣,英武之气溢于眉梢。胡亥心中一动,只觉这女子就其容貌而言,也不是特别出色,虽然如此,六宫粉黛之中,何曾有这般品格?
正胡思乱想,无名进入正厅,一个长揖,朗声道:“天元棋院掌门无名,率师妹雅韵,见过王爷千岁。”
蜀王笼络能人异士这一套,平日都是做惯了的,顿时还礼不迭,呵呵大笑道:“何必如此多礼?大驾光临,蓬壁生辉,我府上棋客久闻兄台风采,昨晚抱憾未能会面,今天都来见识一下呢。”一面说笑一面将二位让入上座,雅韵抱着匣子,却不落座,只在无名身后侍立。却把蜀王身后的胡亥给急了个死,恨只恨这浪得虚名的无名好生托大——这不简直就是唐突佳人么?
蜀王身后诸多棋客同时拱手道:“久仰阁下大名,如雷灌耳,今日相见,三生有幸!”只是这群人当中倒有好几位身形魁梧、虎背熊腰,原是胡亥带来的大内侍卫,不放心九五之尊,改扮了前来护驾,倒把无名给看得呆了。此时外面早已献上茶来,只见那一个描金填彩红漆茶盘里装着三盏龙井,却正托在扮作小厮的银河手中,一直送将过来。
胡亥看银河堪堪走入正厅,忽地灵机一动,大踏步走过去。银河不解圣意,忙立定了等候,却见圣天子从盘子里大喇喇取出两盏茶放在几上,这当然是给蜀王和无名的。然后,才又郑郑重重端出一盏,笑嘻嘻地走向雅韵。
雅韵怀里抱着木匣,腾不出手来接茶。这个不用说,也早在吾皇万岁万万岁的洞鉴之中。当下双手一伸,便殷勤着揭开杯盖。
雅韵微微一笑,道:“我还不渴,先放下吧。”这佳人一笑,直笑得圣心如水,波涛动荡,忍不住道:“姑娘不要客气,先饮一口接接风。”说来就来,一举手,将茶杯直向雅韵嘴边送去。
这一来却连无名也惊动了,不免转头去看这等天上地下、绝无仅有的没规矩小厮。主位上蜀王忙咳嗽一声道:“月前听说阁下升任天元棋院掌门,算来正是诸务纷繁的时候,怎么忽然有闲,来到蜀都?“
无名道:“无非是有些家里俗务。说到这个,正要给王爷道恼。在下进都城来,只见四处捕盗,人言纷纷,听说是王爷府中丢了宝物?”
蜀王拨着杯中浮叶,笑道:“可让掌门见笑了。说起来,上个月本王丢了一套御赐金镂玛瑙棋具,乃是本王的镇宅之宝。不过也算不得什么,有劳掌门动问了。”
无名道:“王爷的镇宅之宝,想来必是珍贵的……”
两人这边慢慢切入正题,那边厢却是好戏连台。雅韵心思缜密,行事持重,哪里容得一个小厮跟她歪缠?再说堂堂蜀王府上,规矩何等森严,也不见得就真能出产这种不知礼法的浑人。浑一次还算他是出于意外,焉有接二连三之理?最可恼的是这事从头至尾,蜀王看在眼里,却根本视而不见,分明见得是纵仆调戏。既然如此,与其这样去受人家的气,何如先给他来个下马威?
心念百转间,胡亥将茶往前直送,已到嘴边,笑嗬嗬地道:“姑娘,来……”一句话没有说完,雅韵猛然上身半转,“砰”地一声,怀中木匣正撞在胡亥半边脸上,霎时间真龙天子眼前一黑,腾云驾雾,直向后跌去。
这一下厅上顿时大哗。众侍卫原是一直留意着这边情景,只吃亏在离得稍远,一时拦救不及。此时见胡亥跌出来,连忙飞身去接。一团纷乱中,还夹着“叭”地一声,却是蜀王慌然起立,忙迫中打翻了茶盏。
雅韵却不动声色,岿然抱着木匣,冷笑一声,道:“王爷,尊介无礼,我代你教训了!”
蜀王扭头一看,只见胡亥捂着左脸,正从银河怀中挣出来,知道受伤不重,这才放了心,干笑道:“哪里,哪里……”勉强说了这两句,毕竟皇帝挨揍那是平生未历之事,更何况还是在他这里挨揍?饶是他颇经场面,后面的话还是说不出来。本指望无名站出来代说两句,大家就此下场。往那边一看,无名竟没事人样,端着茶慢吞吞放在几上,顺手还扶起来了蜀王的茶盏,依然接着前面的话题,慢条斯理道:“王爷的镇宅之宝,想来必是珍贵的。不知如今可找到了么?”
蜀王心念电转,自思胡亥出宫这一节,先不能让人知道;而出了宫,却在他府上吃瘪,这一节就更加提都不能提。果然还是这种大事化小、小事化无的处理手法,最合时宜。一念至此,当下挥挥手,将奔上来的众人挥归原位,才向无名道:“现在还没有消息,”只说得这么一句,也不知突然间触动了哪根心肠,一时竟跟这位棋院掌门剖起心曲来,落在座位里,往前一欠身,道:“不瞒掌门说,其实这宝物虽然贵重,但找不找得回,小王也并不是特别稀罕。外面人看见四处捕盗,便以为是小王为了一套棋具而扰动天下。凭良心说,小王虽是个穷王,好歹也是托体先帝,忝列天家,经过多少繁华场面的,眼皮子又怎至于如此之浅?”
“如此说来,王爷原来另有心机?”
“也谈不上什么另有心机,”蜀王苦笑道:“只是这一次也真是古怪得很了。竟隔着几重秘门,连个痕迹也没留下……手段之高妙,真是匪夷所思。如今想一想,还觉后怕。要说小王这片府邸离咸阳不远,他既有这个手段,难说以后不会入宫作乱……所以小王才向圣上讨得旨意,严办此事。这是其一。”
直到这个当口,胡亥才总算将那阵疼痛给挨将过去。要想出这口气吧,一打量,罢咧,真正是时不我待,一转眼沧海桑田,变幻了人间。那厅上一主一客,推心置腹,早已进入丝丝入扣的佳境。胡亥此时此刻,也只能忍了一肚皮的恶气,一把推开银河,还是到蜀王身后站定。虽然气恼,两只眼睛仍然不由自主,直朝着雅韵看去。那姑娘却显然早忘了他,依旧抱匣而立,神情专注,别有一种难言难摩的可爱之处,看在眼里,真是让人又是疼惜,又是愤恨。
胡亥咬着牙齿,却听蜀王越发滔滔汩汩起来,向着无名道:“其二么,就要说到这天下的民风,人心不古也久矣!且别说什么路不拾遗、夜不闭户这种风气,便闭了户,你禁得他扭门撬锁?种种颓风恶习,也都要趁这个机会,好好纠它一纠!所以要借这个题目,杀一儆百,让那天底下的刁民们都看看,凡撞入天家法网,有来无回!这样一番整肃,还怕天下不宁?嗯,虽说以一人之力去挽狂澜,这活儿是艰难了点,可为人臣子的,既要使海晏河清,又岂可畏难而不行?”
无名默然。蜀王羚羊挂角,鸿爪雪泥,不着痕迹地向身后人表过忠心,见眼前人神色间颇不以为然,又虚心地解释道:“小王的这点举措,自己也知道,当然是肤浅得很了。杀一儆百只是治标,若想根治,还需正本清源。设使天下安乐,人民丰足,难道便有天生的贼骨头不成?放着好日子不过,偏要行险窃盗?然而积弊已久,如今也只能一步一步这么走着看了。都说是车到山前必有路,掌门以为如何?”
这番议论倒是光风霁月,颇见着这位天潢贵胄忧国忧民的一片赤忱。只可惜他背后的那位主儿,却是坐惯朝堂的人,两只耳朵只没被忧国忧民磨出茧子来,这当儿却哪里耐烦再听这种腔调?实在没得消遣,只得仍旧去看雅韵。雅韵本来眼皮微垂,一直看着厅中一片水磨青砖。听了这句话,眼珠子一动,转了道弧线,却去看坐在她眼皮子底下的无名。
从这个角度去看无名,当然也看不见什么。落在眼里的,无非是天元掌门的一个侧脸。这个侧脸如今正在沉吟,沉吟得雅韵脸上不期然透出一片着紧。按说这表情也很细微,无奈胡亥天纵英明,又一脚跌进情天恨海,那双眼睛也就自动变成省视牙雕的放大镜。骤然看见,蓦地里心头一亮,霎时间翻酸江,泼醋海,心里就直叫起来,呜呼,昊天罔极!原来这妮子、这妮子……
无名沉吟半晌,终于道:“王爷既然问起,实不相瞒,在下这次造访,便是想为这些人,在王爷跟前讨个情。说到国家大事,在下是不懂的。在下只是个江湖棋客,只知道一句老话,我不欲人之加诸我者,吾也欲无加诸人。象杀一儆百这种举措,做起来自然爽快,只是不知天底下,有谁愿意去做这样的‘一’呢?不止死非其罪,也是罚过其罪。在下不愿意做,想来王爷也未必是愿意的。”
这番话只第一句,蜀王听着就不对,接下去,越听越不是味道。好容易听完了,勉强笑道:“没想到掌门大好男儿,倒也有这样的妇人之仁。”
无名道:“原来天理国法,在王爷眼里只是妇人之仁。”
蜀王怫然道:“掌门这是何意?须知小王这次的差使,是奉了旨意的。怎么叫做没有天理国法?”
“那么王爷以为,圣旨便是天理国法?”
蜀王一怔,道:“这种话,却教小王不好回答了。按说朝廷既拜有谏臣,便是承认即使是圣意,也未必就没有舛错。然而说到圣旨,掌门若还以为不够天理国法,大可以入京面圣,当廷辩驳。在这里指斥,小王却未免有些肩膀单薄,挑不起来。”
“既然王爷担不了干系,在下曾受先帝恩赐丹书铁券,自要入宫陛见,拜求免罪金牌。”
这句说得着着实实地语惊四座,厅内诸人包括雅韵在内,心里都是一紧。莫名紧张中,只听无名缓缓道:“所以如今只求王爷手下留情,暂缓用刑。好歹等在下这么几天,那么倘若圣上一时恩准,还可以多少留下几条性命。”
PS:胡亥剧照

转载请注明出处。

 相关文章
相关文章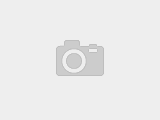

 精彩导读
精彩导读 热门资讯
热门资讯 关注我们
关注我们

